律界风云
浅谈猥亵儿童罪的犯罪构成
浅谈猥亵儿童罪的犯罪构成
作者:许学斌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猥亵儿童罪的法律定义、构成要件、处罚规定及其对儿童权益保护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儿童安全问题愈发受到关注,对猥亵儿童行为的惩治也成为了社会热点话题。文章通过分析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案例,阐释了猥亵儿童罪在刑法中的地位,并指出了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猥亵儿童罪的规定及其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儿童保护法律体系的建议。文章认为,强化法律意识、完善立法、提高司法效率和儿童自我保护教育是保护儿童免受猥亵之害的有效途径。
引言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安全和健康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猥亵儿童罪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条款,旨在保护儿童身心发育不受侵害。然而,由于社会观念的变化和法律环境的不断发展,对猥亵儿童行为的界定、处罚和预防措施也面临新的挑战。本文将深入剖析猥亵儿童罪的相关法律问题,以期为儿童权益保护提供更为有效的法治保障。
一、猥亵儿童罪的定义与构成要件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之“猥亵儿童的”罪状,猥亵儿童罪指故意对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以奸淫幼女之外的方式进行性侵犯的行为。因为不满十四周岁儿童尚未形成健全的性意识选择防范能力,需要运用法规范和儿童性禁忌规范特别保护。对儿童实施刺激、满足性欲的行为,即认为属于儿童不能够识别选择防范的性行为,即认为具有对儿童性侵犯的性质,即是猥亵儿童的犯罪行为。鉴于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故猥亵儿童罪不包含奸淫幼女方式的性侵犯行为。据此,猥亵儿童罪可以简单定义为:故意性侵儿童的行为,其构成要件如下:
(一)猥亵儿童罪的客观要件:猥亵儿童行为
猥亵儿童行为,是指对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实施性侵犯行为。鉴于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准确说,猥亵儿童行为,指奸淫幼女之外的对儿童实施性侵犯行为。其中,“性侵犯行为”,是以普通成人性观念为标准认为的具有刺激、兴奋、满足性欲的行为。因为婴幼儿尚未形成性意识,不能理解性意义。十岁左右的儿童,虽然开始逐渐形成性意识,但不具有成熟的性识别选择防范能力。所以,尽管猥亵的对象是儿童,但评判行为性侵犯的标准是普通成人的性观念。按照普通成人性观念的标准,对儿童实施具有刺激兴奋满足性欲的行为,就是对儿童猥亵行为,也就是对儿童性侵犯的行为,主要包括以下情况:1.对儿童性器官或性敏感部位的侵犯;2.对儿童实行常识意义的性行为,如鸡奸、手淫、(与男童)性交、以性器官、性敏感部位磨蹭儿童身体;3.使儿童自行实施第1、2中的性行为或观看自己或他人实施第1、2中的性行为。
其中,“性侵犯”不以被害儿童当时感知性侵犯事实及性质为必要。婴幼儿没有形成性意识,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逾越了与儿童亲昵界限、普通人看来具有性侵犯性质,即可认定为猥亵儿童行为。性意识形成中的儿童,虽然对性意义有一定程度的感知,但鉴于儿童身心尚未成熟,即使行为没有令其产生性羞耻感,也可以认定为猥亵行为。当然,令儿童产生性羞耻感的行为通常足以认为具有猥亵性质。
尽管儿童遭遇行为人实施的性意义行为之时没有性意识或没有性羞耻感,但仍然遭受到性侵害。因为儿童遭遇性意义行为的情形可能留在意识、记忆里,对其未来成长、人格形成发生持续的侵害或负面影响。有的性侵行为可能对儿童身体造成伤害,也会对其未来健康成长造成负面影响。
(二)猥亵儿童罪的主观要件
1.猥亵儿童的故意。根据刑法第十四条第二款“故意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和第十五条第二款“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猥亵儿童罪是故意犯,即以故意为主观构成要件。猥亵儿童罪的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了猥亵儿童的行为(事实)。行为人把未满十四周岁的儿童误认为已满十四周岁而与之发生“自愿”猥亵行为的,因缺少猥亵儿童的故意,不构成犯罪。对于误信为儿童而实施猥亵行为的,不能认定存在该罪的构成要件该当事实,有观点认为可成立未遂犯。⑴因为我国治安处罚法也规定有猥亵儿童的治安违法行为,对于这种情况没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给予治安处罚就已经很充分了。
关于猥亵儿童故意的认定,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幼女(儿童)年龄是否达到十二周岁为标准,分别予以指导和规范。《意见》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十二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也就是说,即使被害人身体发育、言谈举止等呈早熟特征,行为人亦辩称其误认被害人已满十四周岁,也不应采信其辩解。”《意见》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对于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观察可能是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一是客观上被害人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生活作息规律等特征确实接近成年人;二是必须确有证据或者合理依据证明行为人根本不可能知道被害人是幼女;三是行为人已经足够谨慎行事,仍然对幼女年龄产生了误认,即使其他正常人处在行为人的场合,也难以避免这种错误判断。”《意见》第十九条认定行为人明知“幼女”规定同样适用于猥亵儿童罪案件中认定明知对方是“儿童”。
2.猥亵儿童罪不应当被解释为“倾向犯”。对于猥亵儿童罪是否属于“倾向犯”,即是否以行为人“为了刺激、满足性欲”的动机或内心倾向为主观要件,需要特别阐述。因为关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是否为倾向犯……对此问题,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均颇有争议。
“传统观点以及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持肯定态度,要求本罪主观上具有刺激或者满足性欲的内心倾向。”侮辱妇女,“这里的猥亵……满足自己性欲或挑逗他人引起性兴奋和满足,有碍身心健康的性侵犯行为。”从立法历史发展过程看,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流氓罪分解,“分别规定为若干独立的罪名”,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就是源自流氓罪中“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的基本内容。流氓罪成立以流氓动机为要件,是倾向犯,猥亵罪与流氓罪的渊源关系自然导致学说将猥亵罪解释为倾向犯。这种立法演变轨迹,在学术文献中依然可见,例如,“侮辱妇女,即是指行为人基于流氓动机,针对不特定的妇女使用或实施的各种淫秽下流的语言或动作,致使妇女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我国刑法规定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中的‘猥亵’的含义可以界定为:‘猥亵’是以妇女为侵害对象而实施的,能够刺激、兴奋、满足行为人或第三人性欲,损害善良的社会习俗,违反良好的性道德价值观念,且不属于奸淫妇女但又具有明显的‘性’内容的行为。”立法修订的影响只是措词由“流氓动机”变为“为了刺激或满足性欲”或者“为了性刺激”。司法实务中,猥亵罪的判决书中往往会出现“为了追求性刺激”之类的判词以表明具备猥亵主观倾向要件。
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说、实务曾广泛采取猥亵罪倾向犯说。“行为人所为的行为在客观上若不能认为系基于色欲的一种动作,而且在行为人主观上亦非是为了刺激或满足其本人性欲的行为,即非为猥亵行为”“行为人除了故意之外,还必须出于“淫欲的满足才能成立的犯罪。忽视这种心理倾向而作解释,法律的运作就成了‘说文解字’。”⑻台湾地区的学说、实务一定程度上反映欧陆学说和实务。“本罪需要是以作为行为人的猥亵性主观倾向的表现而实施的(倾向犯),即需要是在刺激行为人的性欲、使其兴奋或者使其满足的意图之下实施的,因此,例如,只是以报复或者侮辱、虐待的目的实施胁迫女子,使其裸体后进行摄影的行为,虽然成立强要罪,但是,不构成本罪”“判例认为,本罪是倾向犯,要求是在“刺激、兴奋或者满足犯人的性欲这种性意图之下实施了猥亵行为,因而,即便是出于报复的目的,让被害女性裸体之后,再拍摄其裸照的,也不构成本罪。”
日本新近的学说逐渐采取否定倾向犯的观点,如“有学说提出,这种所谓的‘性意图’,与是否侵害了作为保护法益的性的自由毫无关系,因而,无须此要件,这种观点是妥当的。”或许是受其影响,我国学者渐有否定倾向犯观点,由此而引起关于猥亵罪是否为倾向犯的争论。
否定说作为新说,首先,立足于法益侵害说的客观取向,认为猥亵对性自主权(法益)侵害是客观的,行为人无论是否出于刺激或者满足性欲的倾向,其猥亵行为都侵犯了性自主权,与猥亵行为人主观倾向无关。其次,否定说认为,不要猥亵(刺激或满足性欲的)内心倾向,完全可以从客观上认定猥亵行为,区分罪与非罪、猥亵罪与侮辱罪,不会导致客观归罪。⒀再次,否定说认为,以(刺激或满足性欲的)内心倾向为要件,反倒会不当扩大或缩小处罚的范围。
肯定说则针对否定说的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首先,如果立足于规范违反说,重视行为本身反伦理性与行为人内心的恶性,应当肯定猥亵罪是倾向犯。如“客观上是相同的脱光妇女衣服的行为,如果是出于诊断或治疗的目的,就不构成犯罪;如果是出于刺激或满足性欲,则可能构成犯罪。所以,倾向犯中的内心倾向,根据内心倾向的有无,法益侵害性显著低下的场合,可以解释为影响违法性。”⒂其次,确立刺激或满足性欲内心倾向要件,有利于认定猥亵行为,有利于区分猥亵罪与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侮辱罪的界限。对于不能认定猥亵倾向的,还可以按照侮辱罪定罪处罚,不至于不当扩大或缩小处罚范围。
针对肯定说的反驳,否定说进一步论证:“肯定说以行为人的内心倾向作为定罪的基础的非客观性,背离了我国刑法所坚持的客观主义的刑法观。”“强制猥亵罪不是行为人违反抑制性欲义务的犯罪,而是侵害作为被害人法益的性自由的犯罪,”因此只要侵犯了性自由“不管行为人的内心倾向如何,都应当认为成立本罪。”前述是否倾向犯之争主要围绕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进行的,就猥亵儿童罪来说,同样存在是否倾向犯的问题。
笔者主张,不应当将猥亵儿童罪解释为倾向犯,不以行为人具有刺激、满足性欲内心倾向或动机作为主观要件,理由如下:
从法规范解释角度讲,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没有明文规定猥亵儿童罪需以刺激或满足性欲之类的动机为要件。那么,是否有必要将其作为不成文要件呢?笔者认为,也没有必要。首先,客观上对儿童实施性行为,因为儿童没有性的识别选择防护能力,按照社会成人一般观念认为该行为具有性意义即刺激、满足性欲的性质,即违反了儿童性禁忌规范,足以危害儿童身心健全成长,构成对儿童的猥亵或性侵犯。其次,行为人主观上对自己对儿童实施的性行为事实有认知,同时应当认知到自己的行为违反儿童性禁忌,具有性侵儿童的故意和危害性认识。
从司法认定角度讲,行为人对儿童实施刺激、满足性欲的行为,即具有性意义的行为,即具有性侵犯性质的猥亵行为。刺激、满足性欲是根据成人一般性观念对行为客观性质的判断,而不是对行为人主观动机判断。常人看来刺激、满足性欲的行为,就是对儿童实施性意义行为。这种观点在司法实务上也有反映,新近有猥亵儿童罪的判决,已不提“为追求性刺激”之类的判决理由。
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刺激、满足性欲”动机,根据只有两个:其一,被告人供述;其二,根据行为表现推断。被告人供述不可信,其实只能是依据行为表现认定行为是否具有常人看来的刺激、满足性欲的性质。刺激、满足性欲的性质,不能求诸行为人的动机,而只能求诸社会性观念、儿童性禁忌和行为事实。行为人对儿童实施刺激、满足性欲的行为,可以表现或反映出行为人具有性欲动机,但不等于成立猥亵儿童罪以性欲动机为主观要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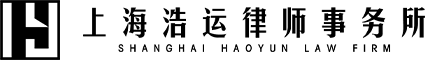
 400-616-5779
400-616-57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