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界风云
从法理角度思考“第三者遗赠案”
从法理角度思考“第三者遗赠案”
作者:郑欢欢
这些年来,社会上出现广受关注的几个“第三者”遗赠案。其中之一是四川泸州的遗赠案。案件大致内容为:四川省泸州市居民王某与蒋某结婚30年,未生育,收养一子。后来,年过六旬的王某与比他小近30岁的李某相识,并在外租房公开非法同居,5年后王某因肝癌晚期,于是立下书面遗嘱,将其财产遗赠给生前与其同居的李某,遗嘱经当地公证机关公证。王某去世后,李某依据王某生前的遗嘱,要求王某的妻子蒋某给付王某所遗赠的财产,遭到蒋某的拒绝,为此,李某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王某的遗嘱系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合法,但是《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遗赠人王某与被告蒋某系结婚多年的夫妻,无论从社会公德的角度,还是从《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编的规定来讲,均应互相扶助,互相忠实,互相尊重。本案中,王某自从认识原告后,长期与其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一条关于一夫一妻的基本原则和第一千零四十二条关于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王某基于与原告的非法同居关系而立下遗嘱,将其遗产赠与原告李某,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行为。
法院认定:王某无视法律规定,违反社会公德,漠视结发夫妻的忠实与扶助,将财产遗赠给与其非法同居的原告李某,实质上损害了被告蒋某合法的财产继承权,破坏了我国实行一夫一妻制度,败坏了社会风气,王某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故对原告李某要求被告蒋某给付遗赠财产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蒋某要求确认该遗嘱无效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一审判决后,李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援引《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同样认定王某的遗赠行为无效,维持原判。
该案是我国近年来非常典型的适用原则断案的判决,对于该判决,有赞同的,认为此案判决正确适用了原则,弥补了规则的漏洞,甚至从道德,社会效果予以褒扬;但也有人认为此案并非依法审判,而是道德审判。由于法律语言和法律规则的局限性,在实践中会有适用法律原则以弥补法律规则的缺陷或者漏洞,以保证案件的正义与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法律对社会的调控能力。我国法律规定以下几点要求,1.适用规则优先,适用原则例外。规则有具体性,僵硬性的特点,而原则有抽象性、灵活性的特点,为了维护法的确定性,一般情况下是应当直接适用法律的规则,而不得放弃现有的法律规则而直接适用法律原则。同时没有特定的理由,法官不能以法律原则来否定现有的法律规则,只有法律规则存在漏洞或者缺陷时,法律原则才可以作为审判依据发挥作用;2.为实现个案正义,方适用法律原则。司法裁判既要保障法的安定性,以维护形式正义,又要顾及个案判决的正义性,以实现实质上的正义,在实践中,当出现适用法律规则审判具体案件会导致极端的不正义不公平时,方可以舍弃法律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这是牺牲法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为代价的;3.适用法律原则应履行充分的说理义务。法律原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作为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调节器”出现在司法裁判中的,要真正实现此项目的和功能,还取决于用原则断案时的说理和论证,以促使价值判断的客观化,减小原则适用中的恣意的可能。
本案判决适用“民法典基本规定编”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基本原则,而放弃了“民法典继承编”上的明确规则。《继承编》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和个人”。法院最终依据基本原则判定王某的遗赠行为违反民法的基本原则,损害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即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行为,从而作出王某遗嘱无效的判决,其实质是突破法律规则的明确规定,而直接适用法律原则。
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涉及到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的适用界限,法院应适用我国“民法典继承编”的具体法律规则认定遗嘱有效还是适用公序良俗认定遗嘱无效,个人有以下几点看法:
1.关于“民法典继承编”相关法律规定,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和个人。”本案中,遗嘱人根据我国《民法典》的具体规定,行使其处分个人财产的权利,立下遗嘱,并到公证处进行公证。遗嘱人立遗嘱时是完全民事行为人,该遗嘱符合其真实意思表示,客观上符合遗嘱的形式要求,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关于特留份额的规定,也没有出现使遗嘱无效的情形。因此,遗嘱人的公证遗嘱是完全有效的。
2.公序良俗原则。关于公序良俗原则,法律上并没有一个精准的概念,各国对此相关规定也不尽相同,这一规定不论是内涵上还是外延上都很模糊,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这给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随着社会发展,即使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域,人们对道德衡量以及风俗习惯都很大不同,想必不同的法官对公序良俗的理解也不一致。
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我国宪法第33条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平等的享有法律权利,平等的履行法律义务,违反法律时,公民平等地受到法律的追究,任何人不得享有特权。遵循这一原则,那么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应当平等的保护第三者的遗嘱继承权。
4.关于意思自治原则。我国法律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本案中,遗嘱人有自由订立遗嘱的自由。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遗嘱人到公证处进行遗嘱公证,真实表达其意思表示,这些都是基于法律的相关规定及对当事人法律的信任。
5.关于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应用于个案当中,如果一条规则所规定的事实是既定的或者这条规则是有效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接受该条规则所提供的解决办法,或者该条规则是无效的,那么该规则对裁判不起任何作用,法律规则为公民提供一种确定的行为指导原则,于是,公民按照法律的规定作为或不作为,法律规则为公民的行为提供一种确定的预期;法律原则不同,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法律原则都可以共存于一部法律,当两个法律原则在个案中发生冲突时,法官必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有关背景在不同的法律原则间做权衡,强度较高的原则对案件具有指导作用,而另一个并不必然失效。
其实,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就是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权的关系,穷尽规则方可适用法律原则。法律原则是贯穿整个法律体系的精神,是法律规则的灵魂,但是其适用必须遵循严格的条件限制,在有具体的法律规则可供适用时,我们不能直接跳过法律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本案判决固然考虑到了保护婚姻家庭的利益,维护社会公德的原则,却尚未充分重视法的安定性以及遗嘱自由的原则。
我国法律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原则以及夫妻间相互尊重的原则,但本案是一个遗嘱继承案件,在有具体的法律规则可供适用时,我们不能跳过法律规则而直接适用法律原则。因此公序良俗的原则与遗嘱自由原则在内容与适用上存在冲突。在现如今我国公民法律信仰普遍缺失的情况下,我们更应当保护法律的稳定性,保护公民的法律信仰,鼓励公民按照法律规则行事。遗嘱自由是为了保障遗嘱人能够自由处分身后财产而不受他人约束,本案中遗嘱人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将身后财产赠与原告,遵循了《民法典》中意志自由的理论,这种赠与行为应受法律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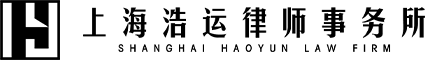
 400-616-5779
400-616-5779



